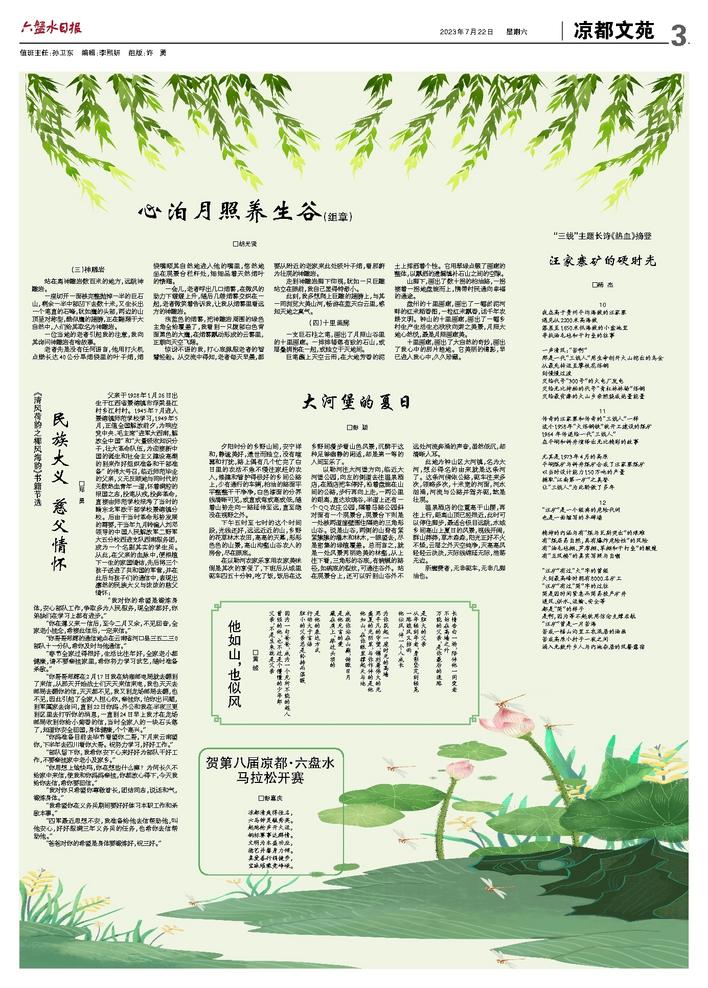□杨 杰
10
我在高于贵州平均海拔的汪家寨
遇见从2200米高海拔
落差至1650米低海拔的小盆地里
寻找油毛毡和干打垒的往事
一声清风:“苦啊”
那是一代“三线人”用生命刨开大山挖出的乌金
从最先转运至攀枝花炼钢
到慢慢过渡
交给代号“300号”的火电厂发电
交给无比神秘的代号“青杠林林场”炼钢
交给最贫瘠的大山乡亲燃烧成热量能量
11
传奇的汪家寨和传奇的“三线人”一样
这个1958年“大炼钢铁”就开工建设的煤矿
1964 年传递给一代“三线人”
在平峒和斜井演绎出无比精彩的故事
尤其是1973年4月的高原
平峒煤矿与斜井煤矿合成了汪家寨煤矿
以当时设计能力150万吨的产量
摘取“江南第一矿”之美誉
让“三线人”为此骄傲了多年
12
“汪矿”是一个经典的危险代词
也是一面缩写的丰碑墙
精神的内涵与有“煤与瓦斯突出”的艰难
有“煤层易自燃,具有爆炸危险性”的风险
有“油毛毡棚、芦席棚、草棚和干打垒”的酸楚
有“五风楼”的真实写照与自嘲
“汪矿”有过“大”字的曾经
大到最高峰时拥有8000名矿工
“汪矿”有过“简”字的过往
简是因时间紧急而简易投产矿井
通风、供水、运输、安全等
都是“简”的样子
是啊,因为等不起就用信念支撑启航
“汪矿”曾是一片苦海
苦成一幅山沟里工农混居的油画
苦成高原小村子一夜之间
涌入无数外乡人与内地杂居的风餐露宿